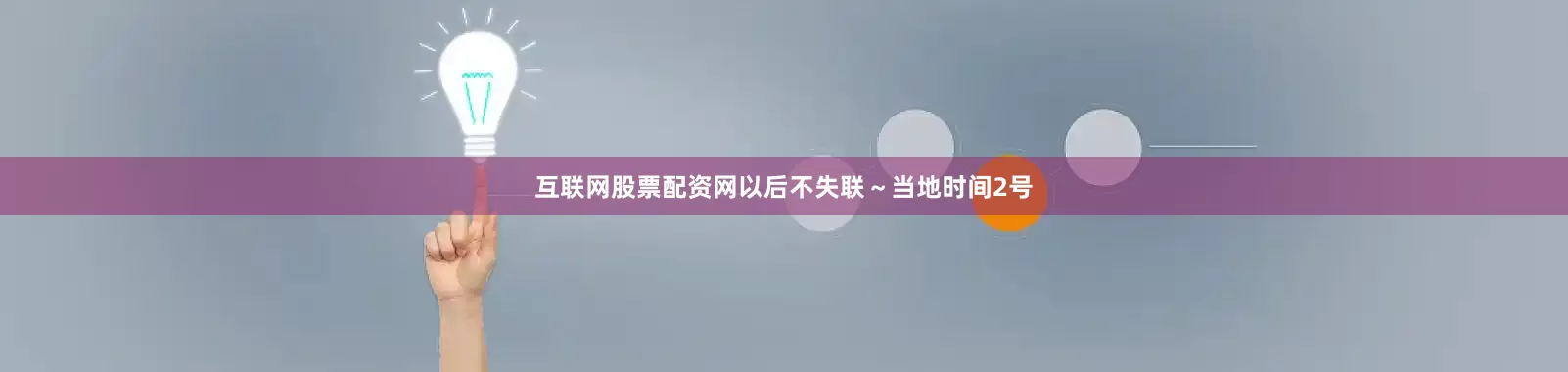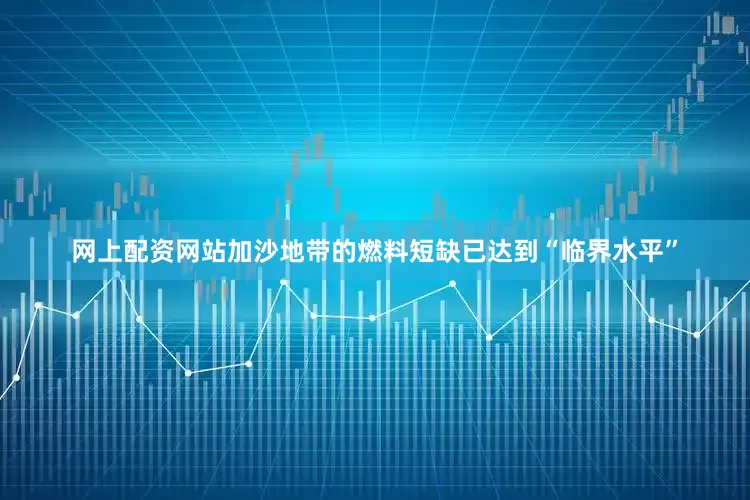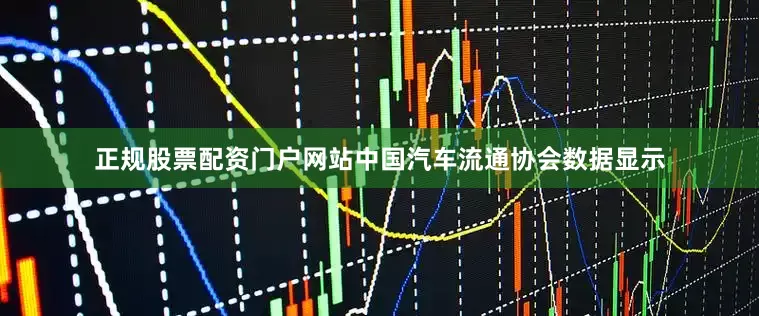青山深处,一座百年老屋改建的客栈,包容着人世间所有的失魂落魄者:痛失挚爱的客栈主人、患病失恋的顾客、从城市返乡的年轻姑娘们、进行田野调查的科学工作者、背负沉重历史的一对老夫妻、毕业季分手旅行的大学生们……青山栈在所有人走得跌跌撞撞的时候,扶了他们一把。
作家蒋韵最新长篇小说《在山那边》,以客栈主人丧妻后创建青山栈的故事为主线,串联起来来往往的旅人故事,从民国到当代,不同代际的人群,故事动人心弦。里尔克的诗句“我们只是路过万物,像一阵风吹过”在小说里多次出现,显然是作家寄寓深意。最初这部小说的副标题是“献给死亡”,那本来是蒋韵写作《在山那边》的初衷。但最后她改成了“献给漂泊者”。
《在山那边》,蒋韵著,上海文艺出版社2025年4月出版
“要说特殊,也没什么特殊的,所有的生命不都是‘路过’吗?”蒋韵觉得,“路过”才是本质。“漂泊”也是。之所以没有写“献给死亡”,是她深知自己对死亡的感知、思考、理解尚显肤浅,所以放弃了。
中华读书报:小说以青山栈为背景,所有青山栈的过客都有各自的隐痛,而青山栈成了他们疗愈的所在。您是在什么背景下完成的这部小说?希望在作品中表达什么?
蒋韵:以客栈或者民宿为场景写一篇小说,这想法其实由来已久,只不过好像一直没有等到机会。2021年秋冬之际,我意外地经历了一段黑暗的日子。当我极其侥幸地从那段日子里走出来后,忽然就有了写《青山栈》的冲动:这其实也是这部小说一开始的名字。我不很清晰我要在这小说里表达什么,尽管此时的我特别感恩命运的眷顾和厚待,但说实话我并没有那种经历了生死之后醍醐灌顶的大彻大悟,没有那些深刻深邃深沉的哲思,我只是感到特别深的疲倦。所以,我不过是在写我的向往,写一种幻想,幻想大地上可以有这样一个所在,一个方寸之地,能容纳几个从生活中出逃的人。我其实从来都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家,我深知现实的人世间没有这样的地方,那我就创造一个。对我而言,这就是小说的意义,无中生有。很多年前,在我还年轻时,喜欢过俄国表现主义戏剧大师梅耶荷德,他创立了“假设性本质”的戏剧理论,拒绝演员在舞台上像猴子一样模仿现实生活,他说那很羞耻。这话当时让我十分震惊,且深深影响了我,又或者,它唤醒了我内心的什么东西,可能伏笔从那时候就埋下了。青山栈是什么?藏在大山深处的一个极不真实的小小乌托邦,仅此而已吧。
中华读书报:《在山那边》书写了不同代际的感情生活,故事层次较多,但不那么复杂。这部小说在您的所有作品中是否没有太大难度?
蒋韵:应该说,是我没有完成好才对。我在写作之初其实是有一点野心的,那也是我写《青山栈》的契机之一:有一天我很偶然地看见了一套书《中国外来入侵植物志》,我当然知道入侵植物、外来植物啥的,但是当这样一套皇皇巨著突然出现在眼前,感受还是非常不同。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晰地意识到,我的位置原来是在它们的对面。这让我有点警觉。入侵植物的命名和划分,是以我们人类的视角、立场和利害。那地球的视角呢?植物们的视角呢?在没有人类之前,谁是地球上的原住民?当然,我还没有愚蠢到要为植物或者地球代言,那也未免太狂妄太自不量力,我只是希望自己作为人类的一员能超越一些,抛掉人类的功利去写写那些从远方漂泊而来的植物们,不管人类怎样命名它们,称它们是敌是友,是利是害,我只想知道它们的故乡在哪里,又是以何种方式来到了我们的土地上,最终怎样落脚生根,繁衍生息。我想选择性地写几种北方大山里这一类的植物,来呼应小说里人物的命运。就像“青山栈故事汇”一样独立成章,冠名“山区植物谱”,写北方大山对这些漂泊而来的种子,这些流浪生命的仁慈和接纳。那段时间我沉浸其中特别入迷,为此读了一些书,还辗转托朋友联系,去北京师范大学拜访了植物学家刘全儒教授,向他请教了最简单的关于入侵植物、归化植物等问题。但后来我还是放弃了,知难而退,因为越深入越敬畏,感到那是太宏大的史诗,知道自己不能造次,知道那是一个目前我还进不去的世界。所以后来只写了人的部分,写青山栈对人的悲伤、悲情、不幸的接纳,而舍去了植物的部分,这样就单薄了很多。至今我还深感遗憾且不甘心,或许,以后我会弥补吧,希望如此。
中华读书报:《在山那边》中延续了《北方厨房》的美食,过油肉、地皮菜、摊鸡蛋、酱梅肉等有山西特色的美食在小说里陆续出现,联想到此前您的许多小说都写到了食物,您很看重食物在小说中的作用?
蒋韵:对,我看重。最早让我意识到这一点的,是一个不知姓名的读者。那是多年前了,有一次我无意中在网上看到了一个读者谈我的小说,其中有一点,大意是说,她还通过蒋韵老师的小说,走近、了解了许多美食,并一一举例说明。我真是无比震惊。我小说里出现的食物,翻来覆去,无非那几样:西红柿炒鸡蛋,酸辣土豆丝,凉拌黄瓜,猪肉韭菜馅儿的饺子……都是为了情节需要所写。可是那位读者说,当这些食物出现在我小说里时,她眼前就会浮现出一个特别鲜明特别美丽的画面,让她没来由地感动,她说那是她的美食启蒙。我挺开心的。我希望我的小说里,有活色生香的味道,有扑面而来的各种气味,有五花八门的声响,有色彩和画面……那是我多年的追求。当然,所有的追求和完成度之间永远都是有差距的。
中华读书报:此前的《北方厨房》将一个北方家庭的烹饪史娓娓道来,写到了“假鱼肚”“桂花年糕”“瓜菜代”“蒸菜蟒”“炸菜角”等几十种食物,还有从1950年代一路走来的充满各种滋味的“味觉记忆”。现实生活中您是不是特别热爱生活、酷爱美食的人?
蒋韵:我总觉得,往往一个人最缺什么,他才最向往什么。我非常羡慕那些热爱生活并且全身心投入和沉浸其中的人。我的热爱在想象之中,完全没有实现和为之付出的能力。我的烹饪水平之低是家人和朋友们公认的,所以,在我女儿那里,家的味道永远都不是妈妈的味道,而是姥姥的味道。可能正是因为这种深深的缺憾,我小说里的好多人物,我喜欢的人物,才有那种我身上所不具备的东西:至死不能被摧毁的诗意,以及,无论何种境遇下都不灭的对生活的尊敬及爱意。走进我的小说中她们简陋的蜗居,你可能会稍稍领略到“诗意的栖居”这句话的意思。总之,她们做着我在现实生活中做不到的事。至少,她们的餐桌上,一粥一饭,一碗一盏,都可体现出她们生活的智慧、审美、爱以及能力。
中华读书报:《在山那边》关注了当下精神生活的复杂多变,从年长者到年轻人,都有各自的烦恼人生,您获取素材的方式是什么?有读者认为这部作品过于“浪漫”,您怎么看?
蒋韵:认为这部作品过于浪漫就对了呀!世界上不会有“青山栈”这样一个地方,我写的是我的一个幻想。我希望大地上有这样一处安静和平的角落,一个诗意的小小乌托邦。我曾经不止一次说过,我不算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家,世界上的小说也不都是现实主义的,但这个虚构的青山栈又存在于现实的生活之中,它迎来送往的一定不是天外来客,它的每一个客人步履上都带着现实生活中厚厚的尘埃和泥泞。我觉得这恰恰就是特别有意思有意味的地方。我的“青山栈故事汇”里,有两个故事雏形都来自我女儿,是她很随意讲给我听的,当然它们被我改造得面目全非。我女儿看了说,要是我,我肯定不这样写。可我就这样写了,这算是我取材的方法之一吧。如今我们生活的时代,要想做到闭目塞听还真不太容易,只要你有一个手机,你就得被迫接受太多的讯息。我不是一个排斥手机的人,我喜欢在手机里刷小视频,也关注了很多陌生人,有开大货车冷柜车的司机,有云贵大山里的普通农家,有陕西农村、山西黄河边、东北大平原、河西走廊、山东沿海各处的人,他们都是普通的农民,在视频号上展示自己的日常生活。除此而外,我也关注时尚博主、艺术家、戏剧演员、国内国外卖房子的、四海穷游的、自驾游的……太多了,数不过来。看别人的生活,尽管是镜头下带表演性质的生活,也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。更有意思的是,“看别人的生活”这件事,渐渐变成了你自己生活的内容。我想,或许在某个时刻,这些会变成我的素材。当然对于我而言,我最想写的,一定是我记忆中最刻骨铭心的东西。
(中华读书报记者 舒晋瑜)
博星优配-博星优配官网-线上配资网站-股市配资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